本土物流业的成本危机链:谁为物流业现状埋单
在物流业复杂而漫长的产业链中,近200万家中国中小运输企业正挣扎在亏损边缘:多头分割的管理、昂贵的税费、运能的膨胀,使得许多本土企业只能靠压低司机工资、超载、套牌等手段来“节约成本”,而这种不得已的短期行为,正严重地损害着物流业未来的健康。 |
0374-3271036
Copyright@2026 Wanli Transport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.
-

万里集团官方微信
-

万里运业官方微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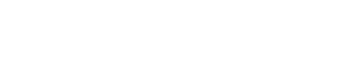





 豫公网安备 41102302000160号
豫公网安备 41102302000160号